在這裡常言「一人不成世界」,所謂世界,實際上就是人的聚合。因此,改變世界,則不外乎改變人,或改變聚合方式,或雙管齊下。
前言世界大部份苦難來自無盡的加害,加害的源頭則是無心者的無心之失。人何以無心,何以行惡?邪惡是先天上與生俱來的特質,還是後天發展而成呢?若用上前篇愚公移山 ---《如何改變社會--- 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中的建構主義和把複雜事情簡化至二元的觀念,大概會傾向相信,邪惡乃是先天大於後天的。
《路西法效應》一書卻告訴我們,邪惡是情境使然。
「大家都是平庸又模稜兩可的惡人。 《馬賽克日本》(2014)
《路西法效應》成書的契機是作者Phillip Zimbardo教授在70年代於史丹福大學所進行的一場本意是研究囚犯在監禁環境下之心理變化的模擬監獄實驗。作者挑選了十多名心智正常的大學生,分別擔任獄卒和囚犯,在兩星期的實驗期間,囚犯穿上囚服,被配上編號,關在由大學地下室改裝而成的模擬監獄,並需要遵守監獄的規定;獄卒則如現實般換上制服,配戴警棍和墨鏡,輪班去維持秩序。為了增加實驗的真實性,作者還特地策劃了一場以假亂真的拘捕行動,安排牧師、家屬親友進行探訪,並舉行了假釋聽證會。
原訂兩星期的實驗,卻在不足一星期內告終。原因是實驗的參與者絕大部份都過份投入角色,讓模擬的監獄變成真正的人間煉獄:獄卒對囚犯惡言相向,動輒把犯人關在名為「黑洞」的隔離囚室,又在報數時分刻意要求犯人做出侮辱性的言行;更先後有囚犯抵受不住壓力而崩潰。身為典獄長的作者亦當局者迷,一心想著完成實驗,一度拒絕承認囚犯崩潰、家長憂心等指向實驗失控的表徵。最終作者被前來參觀實驗的女友一言驚醒;研究的重點亦由囚犯轉至獄卒以至其他人員的轉變之上。
身為局外人,難免會嘀咕,囚犯明明有權退出實驗,為何仍甘願留在模擬監獄裡受盡屈辱、折磨?獄卒本為心地善良的大好青年,何以會出現180度的轉變,變得如此冷血?作者身為學者,又何以會容許實驗變得荒腔走板?
一切也源於角色的內化。
史丹福模擬監獄是一個虛擬世界,一眾參與者為了各自的動機而跳進這個世界的虛擬設定當中,接受新的身份。從實驗的角度來看,假若模擬監獄的環境跟現實相距太遠,參與者則難以投入角色,自然難以取得具建設性的成果。因此為了實驗成果,模糊虛擬和現實的界線,讓參與者投入角色可謂難免。也就是說,實驗的設定本身便帶有一種張力,一方面其本質是「實驗」,另一方面為了追求更好的成果,又要盡力把此種本質的痕跡模糊、隱藏,甚至抹走。作者身為實驗的負責人,理應保持這種張力的平衡,但身兼典獄長的他卻陷於角色的內化,最終弄假成真。
虛擬世界之所以為虛擬,不是說當中的經歷是虛假的;而是說我們在那個虛擬世界的身份,最初是假的。也就是說,這個身份的所作所為,跟現實世界中的那個身份,那個自我,有著某程度上的切割。比方說,我們在遊戲裡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也好,可能我們所扮演的遊戲角色會受警察追捕,但現實中我們卻不需負上任何刑責。監獄實驗,以至一眾虛擬世界的「模擬」、「虛假」之處,正在於原則上,我們可以隨時放下那個虛擬身份而了無牽掛。
我們在現實世界中,也扮演著各種角色:父母、子女、學生、教師、員工、僱主等。某些角色所負的責任會比其他角色為重,比方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的父母,責任則比一個下學後就不用記掛學業的學生為重;另一方面,脫離角色的成本也較高。
但本質上,一切也只不過是角色。
不一定是不可捨割的自我。
誰說父親沒有權利拋妻棄子,放下父親的角色一走了之?(道德上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這些角色之所以不再是隨時可以脫離角色,全因我們從「扮演」變「成為」,把它們內化成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回到實驗的語境,一眾參與者在實驗過後,回復原來的身份,但實驗期間卻是切實地內化成囚犯、獄卒、假釋委員會主席和典獄長。這內化,是同時受著各自的動機和實驗的情境所影響。《路西法效應》的中心主張,正是邪惡並非渾然天成,而是情境使然下,任何人都能內化成惡者。
這份內化,並非身不由己。
是我們主動將角色內化;
或是容許自己被內化。
史丹福模擬監獄實驗的情境,故名思義正是監獄。要瞭解監獄這個情境如何把人化為惡者,首先要替監獄下一個定義。筆者覺得史丹福監獄之所以會產生路西法效應,其本質並非來自困著囚犯的鐵窗、大閘與高牆,亦非監獄裡限制自由的各種規定,而是獄卒之於囚犯的絕對權力與去人性化的環境。在監獄裡,囚犯失去自由、權力,同時也失去了名字。人權、自由、名字,均是人格的一部份。
最初創立監獄系統的本意,是把罪犯困起來,讓他們無力作惡,附以監獄中的待遇作為懲罰;今日的社會比較重視要讓囚犯改過自新,出獄後能夠重新貢獻社會,去人性化的環境,是試圖教導囚犯守規,從而學懂守法。(去人化的環境似乎跟這本意背道而馳)獄卒穿上制服,暫且放下監獄外的身份,被授予權力,成為居於囚犯之上的執法者;自身的道德觀屈服在維持監獄的秩序,執行職務的目標之下。
前言無心者之所以無心,能夠行傷害之事,先要把被害者去人化。書中的進一步解釋是,無視被害者跟我們一樣有感覺、思想、價值以及存在目的。獄卒的權力、被視作低人一等的囚犯、加上高壓而枯燥的環境和雙方的匿名性,種種因素正正提供獄卒們一個去人化的藉口,把囚犯的遭遇視為他們犯罪的自食其果,一切去人化的傷害似乎也是合乎於理,出師有名。
監獄裡頭的社會化也是情境的重要部份。在實驗裡,是某個夜班的獄卒首先在報數環節中加入無理的要求,其他人或見行之有效,或見號令犯人之「趣味」,因而跟從;其餘的獄卒,則是受制於群眾壓力,即使內心充滿掙扎,亦敢怒不敢言。
本書以史丹福模擬監獄實驗為主軸,輔以盧旺達種族屠殺、伊拉克監獄虐囚事件等實例作論據,雖然充滿說明力,成書的本意亦在於擴闊讀者的想像,注意到邪惡離我們不遠,但對於並非身處高壓環境底下的讀者來說,書中的例子或多或少會帶點距離感。
路西法效應只會在監獄此等常人不會進出的地方發生。
社會天下太平,又怎會發生戰爭?
也不會有機會參加這樣特別的實驗罷。
路西法效應只會在監獄此等常人不會進出的地方發生。
社會天下太平,又怎會發生戰爭?
也不會有機會參加這樣特別的實驗罷。
曾在《活出意義來》的讀後感中提到,現實世界也不過是一個大型的集中營。此說並非基於甚麼「身體是意識的囚牢」之類的主張,而是基於現實世界跟監獄相似的本質。
兩者同樣有人的存在。
一樣米養百樣人,筆者相信,在監獄、戰場等特殊環境中,至少仍會有不願同流合污,或是心感愧疚的義人;同樣道理,在監獄外,依然有不少視別人痛苦如無物,損人以利己的無心者。
假若監獄裡頭充滿好獄卒,時刻反省自己有沒有被內化,那裡鐵窗裡頭仍可以是天堂;
若始終也避不開要跟無心者共處、承受他們的加害,那麼就算世界再大,也只不過是個巨大的集中營。
前言監獄本質不在物理上的實體建築,而是在於執法者之於囚犯的絕對權力與去人性化的環境。中共之於香港,正正有絕對的治權。極權的國家機器不需要時刻靠自己動手;它建立了放縱的風氣,放任加害者和流氓在腳下流竄。隱身於人潮之下,我們或能暫且避開獄卒的注目,但獄卒仍然手握大權。
兩者同樣有人的存在。
一樣米養百樣人,筆者相信,在監獄、戰場等特殊環境中,至少仍會有不願同流合污,或是心感愧疚的義人;同樣道理,在監獄外,依然有不少視別人痛苦如無物,損人以利己的無心者。
假若監獄裡頭充滿好獄卒,時刻反省自己有沒有被內化,那裡鐵窗裡頭仍可以是天堂;
若始終也避不開要跟無心者共處、承受他們的加害,那麼就算世界再大,也只不過是個巨大的集中營。
前言監獄本質不在物理上的實體建築,而是在於執法者之於囚犯的絕對權力與去人性化的環境。中共之於香港,正正有絕對的治權。極權的國家機器不需要時刻靠自己動手;它建立了放縱的風氣,放任加害者和流氓在腳下流竄。隱身於人潮之下,我們或能暫且避開獄卒的注目,但獄卒仍然手握大權。
不喜談政治的,就來想想後者。即使沒有極權亦步亦趨,去人性化的傷害也不限於監獄,也不是幾顆老鼠屎所為;網絡上滿是活生生的例子,這個博客也寫過不少。
筆者相信,這些加害者的無心不是先天的,而是透過內化而成的;無心者與無心之失,是路西法效應的產物:
從前受盡婆婆晦氣的媳婦,他朝成為別人的婆婆,又重蹈前人的覆轍;
上莊時被上莊批評得體無完膚的下莊,他朝成了別人的上莊,又在周年大會上狠評接任者;
被老一輩看不起的八、九十後,踏入社會後,又覺得00後一代不如一代;
不想成為自己討厭的人,為了搵食,慢慢放下堅持。
看畢全書,筆者想,作者的訊息不是天下烏鴉一樣黑,也不是把人類所犯過的惡行都歸咎於複雜的情境問題之上。現實中,我們亦可見有人能抵著內化的張力和情境因素的壓力,挺身而出;或者至少沒有雪上加霜。同樣是角色內化和情境因素使然,為甚麼惡者沒有內化成一個善待囚犯的好獄卒?
若一切也是情境使然,世界就等於上帝或命運主宰一切,人沒有任何選擇權那般,那麼根本不會有善惡之分。人之所以行惡,只是剛好不幸地陷入一個作惡的情境而已。
此書的珍貴之處,是一份慎思。筆者認為,心理學,以至各種以人類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均是一道道光線。這些光線,以別人的心為鏡,我們因此得以一窺自己的全相。同理,史丹福模擬監獄實驗的研究對象,不是十數個生活於地球另一端的大學生,而是人類;
而是我們自身。
我們必須對惡者有更多的想像。這並不為同情,因為一味同情只會換來心傷;不經反省的無心之失依然不值得原諒 (當然受害一方選擇放下又另作別論)。對惡者要多加想像,因為他們跟我們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不是健全制度下幾隻害群之馬、幾顆老鼠屎。
對惡者要多加想像,因為「他們」可能是「我們」。
情境使然下,我們亦可能淪為下一個加害者。
就是我們一直沒察覺路西法效應的作用,世界的邪惡才得周而復始,循環不息;
甚至我們自己亦投身其中。
讓我們遠離那份邪惡的,也許始於那份慎思。
覺察情境和內化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效用,才能加以防範。
由那份慎思改變我們的善惡觀、世界觀,從而建立更好的歸屬。
更好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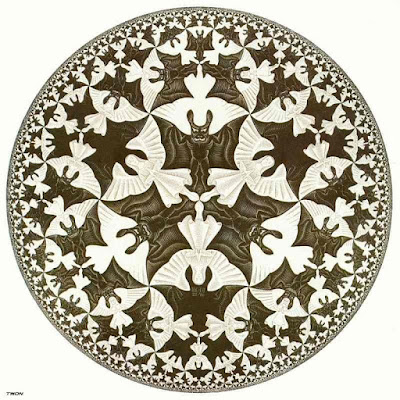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